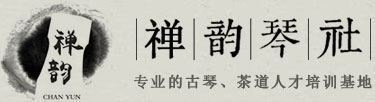古琴之音準,是習琴者常感到頭疼且易起爭議的一個問題。琴之為器,取音無琵琶之品,也無箏之雁柱,..十三徽以供辨位,泛音尚可依徽而取,然按音多有不應徽之音,只在兩徽之分位,如七六:七徽六分,六二:六徽二分等。且明代之前古譜,音位僅標兩徽之間,并未注明具體分位(標徽分之法初始于明)。
即使徽分明確,分數之內尚有厘數,再之肉眼也辨真,各譜多有出入,如七分、七七之辨,故彈琴之人多需練耳,以助徽位之差。因琴家耳力高低不同,修養俗雅有別,便易生仁智之見,琴曲也便分出高下之等,雅俗鄭衛之別

然人心不古,除一片贊揚聲外尚有一些蠅營狗茍之流,亂吐惡臭之氣,惡意中傷兩位先生。其中,“取音不準”便是扣給老先生們的一頂帽子,并大吐什么“該弟子出師后仍需回爐”之惡言。
上海琴家章純青先生的一句話,讓我對于古琴獨特的音準,又有了新的認識。章先生說:“從音樂學角度講,也正是這種不準帶來了其獨有的韻味” 、“我們現在各地的大師,像汪鐸,劉赤誠,謝導秀都是十分出色的,但由于他們和學院派的太過不同,欣賞的人反而很少”,章純青先生從學西樂轉習古琴,能有這樣的見解實屬不易。

對于學院派的風格,自己接觸的少,也無能力去多作研究,但我們提倡毛主席當年所提的 “雙百”(即“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”)方針總是好的,到少要比千人一面,千篇一律等沒有一點藝術個性的情況要好。
其實,如果對中國傳統音樂稍加的了解的琴友,便能對古琴所謂的“取音不準”這一問題,能有清醒的認識。杜亞雄先生將中國傳統音樂大致分為四大類:民間音樂、文人音樂、宗教音樂、宮廷音樂,古琴音樂屬于典型的文人音樂(明清兩朝尤為明顯,如琴、棋、書、畫多為文人所好)。

對于宗教音樂及宮廷音樂等自己了解甚少,不敢妄言,然自己身處山西這一戲曲之鄉,從小耳濡目染,接觸了太多豐富多彩的戲曲,如山西的四大梆子及河南的豫劇,這些鄉音使你不由自主的都會烙上一些烙印,自己尤對上黨梆子及豫劇頗為喜好。
古琴“音準”這一藝術特色,和戲曲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岳父為山西文水人,文水地處晉中地區,所以岳父喜歡中路梆子(即晉劇)。當我閑暇去看望岳父之時,父子倆總有雅興合奏一些曲牌,我拉晉胡(也稱“葫蘆子”),岳夫扯二弦(也稱“二股子”)。

二胡、古箏等弓弦或撥弦樂器常能從戲曲音樂中找到素材,移植成功,我想這正是因為這些樂器能演奏出一些“不準”的音,而鍵盤樂器則不行,如二胡曲《紅軍哥哥回來了》、《秦腔主題隨想曲》、古箏曲《漢江韻》、《秦桑曲》等,試想,如果這些樂曲用鋼琴、電子琴等樂器來演奏,地方風格會那么濃嗎?我想這也是樂曲中某些“不準音”的功勞!
當然,這里所說的“不音準”,并非初學者聽力不佳而造成的毛病,而是由演奏者主觀的藝術理念所造成的,是一種“理性上”的不準確,是對樂曲很嚴謹的一種處理,甚至每次時音高“偏差”的程度都一樣,是一種的固定藝術程式,如學二胡時,老師們常說說“河南音”、“秦腔音”一樣。

這種獨特的藝術處理,放在戲曲里面,便會產生異彩紛呈的流派特色,如放在古琴藝術上便是上文所提及的老前輩獨特的“韻味”!
宋代畫家梁楷的《潑墨仙人圖》是自己非常喜歡的一作品,畫家幾乎沒有對畫面做太多嚴謹的刻畫,只用寥寥數筆,便刻畫出一位憨態可掬、步履蹣跚的仙人形象,極富藝術魅力。

但初學者很難理解畫面中那夸張的頭額及擠在一起的五官,這在繪畫創作中稱之為“減筆”,而非“病筆”,這也是藝術作品和科教掛圖的重要區別!“得意忘形”是傳統文化追求的境界之一,我想,古琴也應如此。
'忙中偷閒'是一種時尚,'琴香茶花'是生活雅事。禪韻琴社,古琴、香道、茶道培訓,采香、煎茶、撫琴?一場身心靈的盛宴,一種洞悉美的.佳生活方式。
門店地址:
曲江店 | 曲江池北路湖城大境天字一號9號樓二單元602
鐘樓店 | 西安北大街西華門(消防隊西邊)宏城..公寓C座1008
高新店 | 科技路灃惠南路中華世紀城D區(中華世紀城小學對面)1號樓一單元301
客服電話:
18710514666 13991316928(微信同號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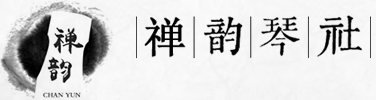


 當前位置:
當前位置: